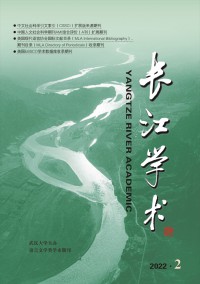學術自由高等教育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學術自由高等教育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有無相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世紀以來,大學開始有限度地介入社會,并逐步從社會的邊緣走到了中心。“每一個較大規(guī)模的現(xiàn)代社會,無論它的政治、經(jīng)濟或宗教制度是什么類型的,都需要建立一個機構來傳遞深奧的知識,分析批判現(xiàn)存的知識,并探索新的學問領域。換言之,凡是需要人們進行理智分析、鑒別、闡述或關注的地方,那里就會有大學”。無論是社會經(jīng)歷涓涓細流般的改革,還是暴風驟雨般的革命,大學都屹立于世,特別是在政治論哲學盛行之時。人們最初進入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做好今后生活的準備,可當他們一旦踏入了大學的校門,就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原來大學和學院就是生活的本身,它們不再是一首插曲,而是成為了主旋律。因此,“大學現(xiàn)在不僅是美國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國生活的中心。它成為僅次于政府的社會的主要服務者和變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導者、推動者和交流中心”。正因如此,宗教和教會此時難以像以往那樣在大學中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隨著工業(yè)革命的廣泛推進,“垂而不死”的資本主義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并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沖擊著教會的枷鎖。隨著大學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對高深學問的追求已經(jīng)從當初的為上帝增加榮耀,轉向了知識本身。大學開始試圖掙脫教會的牢籠,以新的方式認識社會、解釋社會,向世俗化方向發(fā)展。伴隨著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人們源于宗教和神啟的探索發(fā)展到了對世界本身的關注。這一過程的變革方式,是通過嚴厲批判圣書、高舉進化論和新物理學,在暗中破壞主教們建立起來的神圣秩序而進行的。既然如此,大學是不是徹底與教會決裂了呢?毫無疑問,正如大學在獲取教會的特許狀時表現(xiàn)出的對宗教的忠誠一樣,大學實際上是采取了一種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
大學明白,“由于學者完全并且只能是上帝的仆人,因此,其自由是由一個超人的權威批準的。所以宗教信念是學術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特點”。大學天然不是教會,但它卻始終以宗教的虔誠和對上帝和真理的執(zhí)著追求來約束自己。在這個意義上,世俗權力和已有權威并未消退,只是被大學的自我約束機制所取代。這些約束機制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學的學術自由。學術自由的本義,即是作為一種社會機構的大學在不受控制、威脅的情況下對社會的所有方面進行調查和評論。因此,學術自由有其內(nèi)在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從表面上看是掌握了高深知識的“專業(yè)特權階級”服務自我需求的表現(xiàn),但實際上,學術自由最終還是為了公眾利益而存在。社會依靠高等教育機構作為獲得新知識的途徑,并作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資源改進人類生活條件的手段。對個人而言,追求學術自由更是個人道德感的體現(xiàn)。這種道德感與對真理的體悟一起構成了學術自由的信念。學術自由植根于作為學者的專業(yè)團體對高深知識的認識和訓練之中。學術自由是自由的一種特殊情況,它與理智自由相反并僅適用于學術界。學術自由來源于高深學問的性質及其內(nèi)在邏輯,而公民自由則源自于政治原則和契約精神。學術界并不自然遵循民主政治,而是堅守學術本身的規(guī)范。因此,公民的理智自由是每一個公民都享有的權力,而學術自由則成為了作為學術團體的一項特權。強大的教會與作為“特權階級”的學者團體在學術自由上達成的共識是一種“妥善保護”的體現(xiàn)。這種學術保護即是教會對日益壯大的學者社團的妥協(xié),更是學者社團對真理和信念的堅守與執(zhí)著。一旦擁有了學術自由,學者社團便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學者王國,與教會形成了對立。“如果宗教信仰妨礙了一個學者追求真理到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如果他們用神學枷鎖束縛了學術思想,即使很松,那他們也是在那個范圍內(nèi)侵犯了學者王國的自治權”。從此,學者王國開始形成自己的規(guī)范,并用學術自由捍衛(wèi)自身的權利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即便是在教會所屬的大學中亦是如此。因此,北美天主教大學國際聯(lián)合會認為,天主教大學也不應該接受宗教裁判的控制、審查或監(jiān)督。而對教會中的牧師來說,“如果牧師想成為學者,他們就必須擁有學者的傳統(tǒng)學術自由。因為,如果學術研究不是因為學術成就而受到尊重的話,它就不會對教會有任何貢獻”。可見,學術自由已經(jīng)從最初的“妥善保護”轉變?yōu)榻虝蛯W者王國間達成的共識,從而奠定了隨后幾百年來西方大學的靈魂和根基。
二、“有而無在”:作為現(xiàn)代教會的大學
現(xiàn)代大學已經(jīng)成了知識的工廠和現(xiàn)代社會的思想庫。在獨立發(fā)展的軌跡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大學保持著自中世紀以來的傳統(tǒng),同時也鞏固著自身在社會中的核心地位。柏林大學的創(chuàng)立,使人們認識到了大學的社會擔當,認識到了研究對教學的裨益,盡管最生動地把教學和科研結合在一起的是在新大陸上建立起來的現(xiàn)代大學。科學研究使大學重新煥發(fā)了生機,并在與教學的結合中把大學引向深沉。正如杜威所言,對于智慧的信念仿佛變成了本質上是宗教的東西。對通過學者研究獲得的不斷揭示真理的信念,究其本質而言,要比其他任何一種對完美的宗教啟示的信念都更加具有宗教性。在這里,大學教師儼然成為了探求和傳授真理的“高級牧師”,而大學則變成了世俗的大教堂,變成了凈化人類靈魂的場所。人們不再依賴教會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取而代之的是對大學的價值和信念的推崇,并最終產(chǎn)生了對大學的依附心理。“對于許多人來說,大學已經(jīng)成為社會中超自然的機構,因為它似乎發(fā)展著社會的概念。在這里,人們感到自己身后有強大的后盾———學者、學問、書籍、思想和過去”。誠然,這種依附心理最初來源于宗教對人們的啟示。正因如此,大學在認識論和政治論哲學的交替作用下,一方面逐漸走出象牙塔,融入時代和改革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大學也在彷徨和失落中試圖找回教會和宗教曾經(jīng)賦予它的大學精神。大學和學者王國是允許犯錯誤的。“正如從前沒有人會向教皇和身負神授之權的國王提要求一樣,現(xiàn)在也沒有人要求學者事事正確”。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個過程。正如圣•奧古斯丁所說,如果能夠認識的都認識了,那么就沒有犯錯誤的權利了。而學者們所做的,僅僅是追求真理,而從來不是窮盡真理。正因如此,大學的發(fā)展過程總是伴隨著顛簸,但其對真理的執(zhí)著卻未曾改變,“人們在真理方面可以自由犯錯誤的社會,在道德方面優(yōu)越于必須把他們不能理解的東西接受為真理的社會”。伴隨著對真理的追求和大學的擴張,伴隨著科學的革命和學科的形成,知識也開啟了擴張之路,從前居廟堂之高的高深學問也開始以各種形式融入到社會當中。然而大學畢竟還繼承著中世紀以來形成的源自宗教的保守與堅持的一面,大學雖然逐步走向社會的中心地帶,但并不必然地一切都聽從于時代的召喚。正如弗萊克斯納所指出的:“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必須時常給社會一些它需要的東西,而不是社會所想要的東西。”
今日的大學已不再是昨日純粹的學者社團,不再是以保存和傳播知識為己任的邊緣機構。相反,現(xiàn)代的大學是“昔日學術自治、宗教等級與今日的官僚體系的混合體,而這種官僚體系本身又是在學術自治和宗教等級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學術自治和宗教等級仿佛是大學的左膀右臂,為大學保駕護航。與此同時,大學教師作為個體的影響力也引起了人們的反思。無論是梅貽琦的“大學者,大師之謂也”,還是如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Rabi所言“教授們并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雇員,教授們就是哥倫比亞大學”,都表明大學早已被賦予了人格化的特點。大學教授作為高深知識的占有者和傳播者,往往有著超凡的魅力,為社會所敬仰。他們也往往會突破自己的學科限制,對公共事務品頭評足,成為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學者關注社會問題并進行專業(yè)性的反思并無妨,只要是在其自身的研究領域之中,任何問題都可以成為研究的素材。不過,正如社會這個萬花筒一樣,學者們誰也不敢保證自己在每一個領域都能像在自己的專業(yè)之內(nèi)那樣游刃有余。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對教授們的敬畏往往源自他們對公共事務的評論,并把他們對本專業(yè)的權威性移植到其對所有熱點問題的言論上。而教授們往往樂此不疲,并立志從社會的公知變成社會的良知,甚至成為某一派的代表。其實,“魅力非凡的教授必須謹慎小心,不使自己有力的個性發(fā)展成為自己變身‘宗教首領’的起點。相反,他們應該注意當教師和當首領之間的微妙而又重要的差別”。不少教授對非本專業(yè)領域問題的解讀,在某種程度上往往能夠引起社會的共鳴,而專業(yè)的學者往往不會隨便對實事和熱點進行公開解讀,這既是鑒于學術的嚴謹,更是對公眾的負責。而正是有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某些時候引導了公眾輿論的走向,把大學和學術置于尷尬的境地。大學曾經(jīng)彷徨過,也曾徘徊過,因為它曾在物質文明極度發(fā)達的社會進程中迷失了自我方向。
三,結語
因此,現(xiàn)代的大學也急切需要反思自身的行動,并謹慎地在公眾心理的造就者和社會改革的自覺人中間做出選擇。曾幾何時,大學作為一種“世俗的教會”,憑借宗教的力量,一如既往地充當著社會的良心。今天,大學也需要擔負起“造就公眾心靈”的職責。“大學是美國生活中最為崇高、最少腐敗的機構。在我們的全部歷史中,大學和教會一直是為全人類的利益和真理服務的,或者試圖為人類的利益和真理服務的機構。沒有什么機構能擔當起大學的職能,沒有什么機構能夠占據(jù)這個大學已長久地注入了如此多的才智和道德影響的位置”。中世紀之前,教會不僅承擔了德育的功能,也擔負起了智育的功能。隨著大學的興起,智育從教會中分離出來。時至今日,回望大學的千年歷程,大學作為世俗的教會,正同時承擔起德育和智育的職責。大學作為人類的靈魂,仍然延續(xù)著最初的信仰和追求,在時代的洪流中堅守著自己的領地。
作者:江金單位:首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