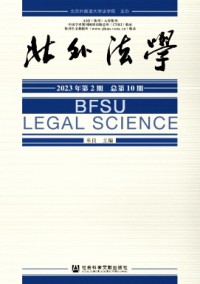法學專家證人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法學專家證人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專家證人在司法過程中的角色因訴訟模式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簡單地說,其核心職能是以所謂“科學”權威的身份使判決獲得正當性。然而,作為判決正當性基礎的科學結論本身也存在正當化問題,當科學的權威性受到挑戰(zhàn)的時候,也就動搖了專家證詞的權威效力。這一現象決定,專家證人無論在查明事實中居于多么重要的地位,都不可能取代法官(或陪審團)對案情事實進行綜合判斷;科學權威更不可能取代司法權威而成為案件的最終裁判者。波斯納指出,司法判決具有權威不在于它們統(tǒng)帥著與科學家的共識相對應的律師們的共識,而在于它是從司法等級的上層傳達下來的。與普通人形成科學信仰時對理性權威的服從相比,與這種政治權威可對應的是等級上層所作的司法決定大致比下層法官對案件的決定更可能是正確的。高層法官的選擇更仔細(一般如此,當然不是每人皆然)上層法官的眼界更寬,此外上層法官還得益于下層法官對案件的思考和律師的額外訴訟摘要和論點。但這種上層正確的假設是無力的。并且即使所有上下層法官意見都一致,他們的決定也比一致的科學判斷少一些內在的說服力,因為法官的方法比起科學家們的方法實在是太虛弱無力了。[1]
司法制度的等級結構以及包含在遵循前例原則中的對穩(wěn)定性的追求也許會在各種意義上促進“正義”:它使司法決定更可為普通大眾所接受,它減少了不確定性,但它阻卻了對真理的探索。于是,當證據、事實、科學意義上真理、及法律意義上的證實這些對于公正性和正當性至關重要的要素不斷受到挑戰(zhàn)而變得模棱兩可時,當價值多元和社會需求的多樣性和客觀真理的不確定性致使判決產生的過程成為判決結果正當性資源時,專家證言便有了獨特的價值,它使裁判建立在科學權威基礎之上從而至少獲得感覺上的正當性。
專家證人的這種角色隨著科學技術發(fā)展的不同階段而發(fā)生嬗變。在西方奴隸制度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科學不發(fā)達,證明手段落后,法官在案情真?zhèn)尾幻鲿r通過人們最信服的神靈來判斷真相,實行神示證據制度,即由神意(或上帝之意)判斷案情,神誓、水審、火審、決斗、卜卦、抽簽等等,使審判獲得合法性。現代科技發(fā)展了收集和審查證據的技術和方法,如形貌顯示與放大技術,組成與結構分析技術,法醫(yī)生物學技術,激光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等;在證據種類方面,視聽資料,即錄音、錄像及計算機存儲的資料都被用來作為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的證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鑒定所涉及的科學已由原有的法醫(yī)學擴展到其他科學,如心理學、考古學、建筑學、化學、毒物學、遺傳學、社會學等等,僅化學就涉及到工程化學、生物化學、物理化學等分支學科。與此相適應,鑒定采用的手段、方法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先進,鑒定結果也越來越準確。如顯微分析法、DNA檢驗法、智商測定法,指紋鑒定可以彩激光、染色劑、激發(fā)能量和化學等方法。鑒定手段、方法的日益科學,降低了審判人員審查判斷的難度,如含量、純度的鑒定,可采用顯色檢驗法、色譜法、分光光度法、顯微結晶實驗以及免疫分析技術,其中有的方法是憑借精密儀器進行的。這些發(fā)展使得鑒定結論等專家證言在現今查明案情中的意義越來越大。[2]于是,曾經在某個時期,人們欣喜地看到,在大量案件中,科學家甚至成為實際的審判者,審判人員直接運用結論意見的數據就可以了。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現代科技的發(fā)展在增加證明手段的同時也增添了更多新型的證明對象,諸如智能型侵權和犯罪劇增(如計算機侵權和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交通、通訊及物理、化學、生物學及生態(tài)學原理作案)、因發(fā)展和利用高科技引起的侵權糾紛(如環(huán)境污染糾紛、高速運行的飛行器和運輸工具造成的侵權、醫(yī)療事故糾紛、專利侵權糾紛)、利用和發(fā)展高科技的合同糾紛(如遙測技術,即計算機和遠距離電信的配合實施遠距離的民事行為,簽訂合同具有即時消滅性,由計算機所記載的交易過程和結果不斷發(fā)生變化,難以保全證據)……法官在運用先進科學技術手段、分析方法的鑒定結論時,不僅僅要審查鑒定經過、鑒定所憑借的儀器、分析方法,確定所得出的數據、鑒定對象的提取與保管是否及時,固定的方法是否安全可靠等,[3]而且常常要在鑒定結論受到挑戰(zhàn)時或在不同的鑒定結論之間進行甄別和選擇,換言之,法官對于專家證詞不僅要進行程序性審查,而且要進行實質性審查。[4]更為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以來,科學失去了對其客觀性的確定感,而裂變?yōu)闊o以數計的次原則和次專家。沒有人還能夠輕易地說有關科學界是什么,更沒有人能夠說科學界是否已經“普遍認可”了某項技術或方法。這種發(fā)展使法官在面對眼前的證據并在相互對立的觀點之間作出判斷并說明其判斷的理由的任務變得復雜起來。現代科學在證明“真理”和正義方面的價值卻受到科學自身合法化的困擾,科學“真理”的多元化使科學權威自身受到挑戰(zhàn),以科學真理面目出現的專家意見在法律權威面前喪失了“權威”地位,于是,專家證言與其他任何證據一樣,都要受到法官自由心證的審查,并由此帶來司法制度的一系列深刻變革。
在美國,根據1923年美國哥倫比亞特區(qū)在“美國訴弗萊爾案”(UnitedStatesv.Frye)中所確立的規(guī)則,科學證據只有在得到有關科學界的“普遍認可”后才能獲得法院的承認,所以科學在審理程序、發(fā)現程序中并非舉足輕重。并且弗萊爾案通過某種陳述方式將決定認可與否的責任轉移到科學界本身,不要求法官對科學的有效性作出判斷,只須被動地聽取“有關科學界”的意見即可。于是,測謊儀、指紋、分光攝像儀、彈道學證據等等都進入了法庭,但看起來十分容易。繼弗萊爾案之后,科學的發(fā)展變得更為復雜、更難以自我證明。自1975年美國證據法規(guī)則頒布以來,法庭上使用的科學數量更大,復雜性更強。根據這一規(guī)則,“所有相關證據都可接納”,包括科學知識,如果有助于對證據的理解或確定爭議的事實以判決事實問題。這里不再要求“為有關科學界所普遍認可”,相反,規(guī)則明顯的措辭表明,至少在聯邦法院系統(tǒng)中弗萊案規(guī)則不再具有有效性。最高法院在1993年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案中正式宣布弗萊案規(guī)則失效。在本案中,法官在評價由雙方當事人傳喚的專家方面的角色消極性減少了,法官須常常涉足于科學問題并獨立作出判斷。最高法院在是否提供專家證據的問題上的結論與《證據規(guī)則》第702條一致,初審法官須作出“對作證所適用的推理或方法是否具有科學有效性以及是否可以適當地用來證明爭議中的事實初步評估”。用大法官Blackmun的話說,最高法院衡量和評論初審法官將這一考慮作為技巧是否為虛假或偽造、是否交同行審查過、其誤差率是否被知悉、以及是否取得了科學界的普遍認可。一個至關重要的變化在于,過去要求法官審查科學家是否認可一項技術,現在則要求法官審查技術的有效性本身。[5]專家在裁判中的地位還受《規(guī)則》第704條第2款規(guī)定的明確限制:“對被告的心理狀況或狀態(tài)作證的專家證人不得就被告是否具有所指控犯罪的心理狀況或狀態(tài)發(fā)表意見或作出推斷。這種根本性的問題專屬于事實裁判者的事項。”這就是本案所涉及的問題,對此,愛德華茲法官指出,這一規(guī)則旨在防止陪審團受專家證人關于被告心理狀態(tài)看法的不當操縱。一種特定的心理狀態(tài)對于一項犯罪指控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陪審團有理由對被告的罪行持不確定態(tài)度,卻被安排聽取聲稱了解被告心理狀態(tài)的專家的意見,那么,陪審團成員們可能依賴于這位政府證人的傾向性經驗來解決他們面臨的模棱兩可的問題。被告心理狀態(tài)的問題具有主觀性,專家的決定并不比陪審員更準確。如果簡單地允許專家來宣告被告的罪行,就沒有什么必要在審判中設陪審團了。
這一變化在更深層意義上改變了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職能分工,引起訴訟模式和一系列程序制度的悄然變革。一方面,英美法官的消極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脅,他們比以前更加積極地參與審查事實和證據,而不再那么信奉波普爾的市場競爭理論,完全等待事實在律師們的相互對抗中“現身”。雖然與職權主義模式下的法官相比,制定法賦予美國法官的傳喚證人的權力形同虛設,[6]但這項法官職權的意義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對于律師聘請專家證人的潛在威懾力,美國的完全“當事人主義”受到法官職權的控制。[7]另一方面,以法官職權調查為特色的大陸法法官面對無法大量難以確定真?zhèn)蔚陌盖槭聦嵑蛠碜援斒氯朔矫娴馁|疑,不再那么肯定地依賴于從前那些由他們傳喚來充當他們技術顧問的專家證人,聰明的法官漸漸地將證明風險轉移給當事人和他們的律師,由當事人雙方對專家證人的證詞進行論證和辯論。法律共同體的成員們開始意識到,認為法院是在尋求真相而且求真是一個不現實的假設,調查事實者對事實精確性以外的其他價值的關切這一點是與司法規(guī)則制定者對規(guī)則真實性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的關切并行的。求真的目的與其它目的-諸如經濟性、保護某些自信、助長某些活動、保護一些憲法規(guī)范-相競爭。因而,程序制度只能在精確和成本之間追求最大的交換值。于是職權主義模式也在向當事人主義方向邁進。
專家證人在中國司法中的角色相當于法官的科學顧問,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專家意見差不多比法官對案件的判斷還要權威。二審法官推翻一審法官的判決、再審法官推翻原審法官的判決、再審案件的再審法官推翻再審法官的判決……常常都依賴于專家證人對事實問題的結論。不同審級的法官之間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上沒有明確的職能分工,再審程序自然更要對原審案件進行全面審查處理,因此,不同的法官便可以就鄰居房屋是否過于臨近原告房屋這樣的問題一次又一次地聘請各自認同的專家證人發(fā)表意見,并各自依據這些鑒定結論做出推翻先前判決的重新判決。科學在證明判決權威性和正當性方面的工具性價值在沒有程序控制的司法體制下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張揚,司法的終局性和權威性卻在這種掩耳盜鈴的“科學證明”中蕩然無存――人們無法想象,依據相互不承認同行權威的專家證人的結論作出的判決可以獲得司法權威!于是,訴訟程序成為法外資源和權力較量的場所,案件一審、二審、發(fā)回重審、再次二審、以及再審、再審、再再審的翻云覆雨中尋求著政治、私利和輿論上的價值。面對以司法資源的巨大投入為代價,以犧牲司法的終局性、正當性和權威性為結局的現實,我們應當反思一下:是否應當對專家證人在司法中角色準確定位、是否應當確立法官在事實判斷方面自由心證原則、是否應當對初審法官和上訴法官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上的職能進行合理分配。
「注釋」
[1]波斯納著:《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
[2]參見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3]何家弘,《證據法學》,1997年版,第438頁。
[4]何家弘,上引,第439頁。
[5]ReformingtheCivilJusticeSystem,editedbyLarryKramer.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6.Page212-234.
[6]參見(美)約翰。萊茲:《為什么美國無法接受德國民事程序中的優(yōu)點》,傅郁林譯,載于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
[7]參見沈達明:《英美證據法》,中信出版社,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