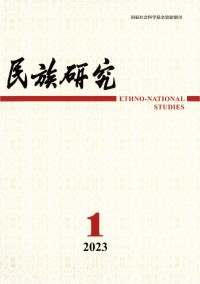民族文學敘事模式演變研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民族文學敘事模式演變研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正名敘事
1978年以后,隨著中國意識形態出現的重大變化,階級斗爭學說逐漸淡出主流,少數民族文學的階級斗爭敘事明顯弱化。1984年,中國文壇興起尋根文學思潮。對于漢族作家而言,文化尋根或許只是中國文學試圖獲得世界文壇認同的一種手段。對于少數民族作家而言,文化尋根則成為民族意識重新喚醒的一個機緣。這一時期,張承志的創作可以說是少數民族作家的一個典型個案。197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1982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黑駿馬》和199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心靈史》顯示出張承志民族意識演變的三個階段。《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雖然以蒙古族生活為題材,但作者的關注點并不是蒙古族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生活歷史。作者通過講述三個故事,塑造了一個蒙古族額吉(母親)的形象,進而回答“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這個問題。第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場春天的白毛風(“暴風雪”)突然降臨,知識青年“我”正在草原放牧中,隨時可能被白毛風吞噬,在萬分危急之際,額吉騎馬趕到,用自己的山羊皮外套為“我”擋住了白毛風,自己卻因為受凍而下肢癱瘓。第二個故事說的是牧場發生了火災,兩個北京知青燒傷了,其中有一個姑娘,傷勢比較嚴重,額吉聽說了這事后,不顧自己下肢的癱瘓,立刻趕到醫院看望受傷的姑娘,給了姑娘巨大的精神安慰。第三個故事說的是草原摔跤手班達拉欽被宣布為階級異己分子并被撤銷了書記的職務,理由是他從小在牧主的蒙古包里長大,是牧主的養子。額吉得知此事后,告訴“我”草原上的一個特殊現象,即“一頂蒙古包下面,有窮人和富人兩種人”,也就是說,作為牧主的養子,并不意味著就具有牧主的剝削身份,額吉提供的經驗經過知識青年們的理性思考,使他們得出結論“,蒙古族社會的剝削現象,經常是在家庭的掩蔽下進行的!”換言之,養子雖然住在牧主家,但他卻是牧主的剝削對象。“養子這種剝削方式是蒙古族社會的一個歷史特點”。這種理性認識使班達拉欽的冤屈終于得到糾正。這三個故事的性質接近,第一個表現了額吉對住在自己蒙古包里的知青的愛,第二個表現了額吉對自己不認識的知青的愛,第三個故事表現了額吉對蒙古族階級同胞的愛。三個故事共同表現了蒙古族母愛的博大。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小說中的第三個故事,涉及到蒙古族階級問題。雖然小說中專門為班達拉欽平了反,但并不意味著作者否認了階級的存在。當然,這個小說的主旨既不是表達蒙古族意識,也不是表達階級意識,它要表達的是這樣的主題:“母親———人民,這是我們生命中的永恒主題!”顯然,在這個小說里,作為回族的張承志,并沒有明顯的本族意識;作為內蒙古草原的插隊知青,他也沒有代蒙古族立言的意思;他努力表達的,是一個超越民族的思想,即“母親———人民”。可以看出,1978年的張承志,還沒有明顯的民族意識,反而有明顯的階級意識。這與小說發表的那個年代的意識形態還是很合拍的。到了《黑駿馬》,情況發生了變化。首先,總體上看,與《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相比,《黑駿馬》的創作意圖發生了重要變化。《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表現的是“母親———人民”主題,這里,無論是“母親”還是“人民”,都只是一個多民族概念,泛指整個中華民族。但是,到了《黑駿馬》,民族意識已經明顯浮出了海面。作者試圖思考“蒙古民歌的起源”、“古歌內在的真正靈魂”,試圖探求“作為牧人心理基本素質的心緒”①,試圖講述“草原古老的生活”①。顯然,這些都是獨屬于蒙古族人的,不像《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那個升華為人民的母親更帶有泛指的性質。其次,小說里有幾個細節,專門寫到男主人公白音寶力格有關“血緣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心理活動。那是當白音寶力格得知索米婭懷上別人的孩子而與之發生沖突的時候,他想喊一聲坐在身旁冷眼旁觀的奶奶,竟喊不出來,他感到了他與奶奶之間的隔膜,“一種真正可怕的念頭破天荒地出現了:我突然想到自己原來并不是這老人親生的骨肉。”②這里,白音寶力格的血緣意識被激發起來了。而在奶奶跟他說了一大番人生的道理之后,他無法認同無法接受,小說寫道“:也許就因為我從根子上講畢竟不是土生土長的牧人,我發現了自己和這里的差異。我不能容忍奶奶習慣了的那草原的習性和它的自然法律……”③這兩段心理描寫表明作者有了明顯的民族意識,親生骨肉代表著血緣,土生土長代表著文化,白音寶力格從血緣和文化兩個因素否定了他與蒙古族的認同,而這兩個因素,恰恰是民族構成的核心因素。張承志在文壇最有影響的小說都是以蒙古族生活為題材的。饒有意味的是,張承志并不是蒙古族人,甚至,也不是漢族人,而是回族人。在《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這個小說中,張承志幾乎是沒有民族意識的,他更多是以一個知青的身份,去體驗他所插隊的地方的百姓的品質。可是,在《黑駿馬》中,他因為小說中人物的情感體驗而產生了民族意識。不過,值得指出的是,這時候,張承志筆下白音寶力格的民族意識并不是他的回族意識,而是“幾年來讀書的習慣漸漸陶冶了我的另一種素質”,即我們可以想象的主流民族或者說是漢族素質。以這種主流素質看,在草原之外,還有一種“更純潔、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業魅力的人生。”④1984年,張承志走進了大西北。在之后六年的時間里,張承志自稱他完成了“脫胎換骨般的改變”⑤。這個“脫胎換骨”的標志,可以理解為他找到了“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⑥;可以理解為“一九八九年秋,我寧靜下來,開始了我的人生爾麥里”⑦;也可以理解為,他成為哲合忍耶的一支筆,寫了一本“他們會不顧死活保護的書”⑧,那就是長篇小說《心靈史》。《心靈史》的出版,表明張承志的回族意識得以復蘇。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終于描寫自己的母族了。”⑨與《黑駿馬》相比,《心靈史》的最大變化就是張承志顯示了他作為回族的強烈的身份認同,有了回族的文化自覺。這種身份認同和文化自覺的一個重要體現,是他對自己原來所接受的主流文化影響有所反思,他獲得了一批回民民間“秘藏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寫下的內部著作”、“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資料”①“、一些文人界外的大作家的秘密鈔本”②。毫無疑問,這些材料對他理解歷史、民族產生了重要影響。張承志的文化轉向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20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思潮中走得最遠的一個作家。如果說阿城、韓少功、王安憶等作家文化尋根的終極目標是深化和壯大中國文學的文化根本,其目的仍是文學追求;那么,張承志的文化尋根則越過了文學,他將自己的文字變成了一個族群的歷史記錄和信仰宣言,從而使文學批評在他的文本面前變得“失語”。③對于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而言,一方面,尋根文學用文化敘事取代了政治敘事,將文學從單一的政治敘事引向了豐富的文化敘事階段。今天來看,尋根型的少數民族文學有一種為其族別寫作正名的沖動。它要找到其民族文化根源,傳達其民族意識,實現其民族認同,將其族別文學從共名狀態中分離出來。另一方面,尋根文學可能導致當代少數民族存在脫離現實、走向封閉的地域文化或民族歷史的傾向。從近20年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看,確實存在這種情形,一些作品自我封閉于民族歷史,割裂了少數民族與整個中華民族的聯系,基本脫離了同時代的主流文化敘事,雖然在展現文化的多樣性方面有較多的成績,但對文化融合,文化包容的一面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
匿名敘事
為什么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第一階段能夠形成與當時主流文化高度認同的共名敘事?根本原因在于,“建國初期在少數民族地區普遍開展了‘’和民主改革運動,得到翻身解放、無償分到土地的那一代少數民族民眾從內心感激共產黨和中央政府。”④階級斗爭理論在當時確實越過了民族意識的籓籬,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普遍認同。為什么第二階段的少數民族文學形成了正名敘事?這也可以從1976年以后的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中尋找原因。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開始了以政治革命為中心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型。最初,這種轉型是全社會受惠。然而,好景持續十多年后,中國開始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這種社會分化是兩個層面的。一個層面是原來財富相對均衡的社會出現了各階層的分化;另一個層面是原來相對平衡的社會出現了欠發達地區和富裕地區的分化。落實到少數民族這個問題,確如馬戎所說“: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就業難和生存難。由于漢語水平低和就業技能弱,他們在與內地來的漢族農民工和漢族大學生競爭時常常受到歧視和排斥……”①階層的分化和地區的分化,成為少數民族文學從主流敘事分離出來的根本原因,雖然它有表現文化多樣性的積極作用,但是,如果這種分離長期持續,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將會產生消極作用。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階層分化和地區分化已經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不穩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階層分化和地區分化已經得到了社會的廣泛的重視,但大多數人沒有注意到,階層分化、地區分化往往與民族問題聯系在一起。一些少數族裔及少數民族地區就在這次社會分化中淪為赤貧,并且失去了社會所應該給予的保護。這種生存現狀使少數民族對主流文化更加疏離,就像馬戎所指出的:“他們很容易把自己的生存困境與族際差異聯系起來,這就使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的民生問題與民族隔閡疊加在一起,從而使西部地區的民族關系更加復雜化。”②也就是說,如今,中國社會幾個嚴重的社會分化問題,如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東部與西部的差距,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差距,貧困階層與富裕階層的差距,這些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都可能隱藏有民族問題在其中,它們互相糾纏在一起,使單一的社會問題變成了復合的社會問題。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備受媒體關注的現象。其一是農民工犯罪現象,比如這些年受到媒體廣泛關注的廣西天等縣溫江村“砍手黨”在珠三角的犯罪事實,人們普遍注意到溫江村的貧困、溫江村人受教育的程度,但有一個情況人們普遍沒有注意,天等縣是典型的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口超過全縣人口百分之九十八。③其二是拐賣兒童以及流浪兒童現象,其中新疆維吾爾族流浪兒童成為媒體關注焦點。其三是鄉村正在淪陷,顯而易見,這些正在淪陷的鄉村,又以少數民族聚居的鄉村首當其沖。值得注意的是,在媒體關注的這些社會現象之前好些年,一批作家已經寫出了相當有影響的同類題材的文學作品。與上述三種現象相關,正好有三個中篇小說涉及了當下媒體關注的領域。它們分別是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凡一平的《撲克》和李約熱的《巡邏記》。《被雨淋濕的河》④描寫了一個叫陳曉雷的農民工,因為各種社會不公而最終走上了抗爭與犯罪的不歸路。這個小說的責任編輯李敬澤曾經撰文回憶他編發這個小說時的心情,當時的他認為,“鬼子對‘現實’的‘描寫’是偏僻的、刺耳的、可能‘越界’的……”,然而,經過六年的多次重讀,他不得不承認,這部作品“拓展了我的世界觀,使我得以接近和理解‘遙遠’的人群———對我來說,他們是遙遠的,遠在我的生活疆界之外———理解他們的生活和心靈,并且意識到那些遙遠的人群隱蔽而確鑿地參與了我的‘現實’的構成。”①李敬澤的話也許有些費解,通俗的理解,大意就是后來中國現實社會發生的各種現象,印證了鬼子小說中的描述,也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巡邏記》②寫的是一個名叫宜江的鄉鎮,這是一個只生長賭徒不生長糧食的地方,男不耕女不織,少不讀書,老不安逸。2010年評論家梁鴻出版了紀實作品《中國在梁莊》,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然而,讀《巡邏記》以及李約熱其他的小說,會看到梁鴻的觀察早已在這些小說中有更細膩、更深入的敘述。李約熱給宜江的賭場取了個頗能給人聯想的名字:珠穆朗瑪,套用梁鴻的思路,也可以說“中國在珠穆朗瑪”。《撲克》③寫的是一個被拐賣的兒童王新云的命運遭際。小說并不像許多相關題材的敘事那樣將重心放在被拐賣兒童喪失親情的悲慘,而是將重心放在了失子父親尋找兒子的過程,以及被拐兒童成年后知道自己身世時的復雜心理。就后者而言,小說的責任編輯李倩倩說過一段話“:‘王新云’一直是處于隱匿狀態的,他隱藏了自己的身世,且隱蔽在一段越軌的愛情當中。這又恰恰說明了,在個人私密空間日益縮小、社會信息空間日益擴大的今天,隱匿是現代城市人的一種生存狀態。”④隱匿是現代城市人的一種生存狀態。李倩倩這句話其實是一個重要提醒,提醒我們注意上面三部作品作者的身份。《被雨淋濕的河》的作者鬼子是仫佬族,《巡邏記》的作者李約熱和《撲克》的作者凡一平都是壯族。然而,閱讀這三篇已經產生重要影響的小說,人們會發現,原來我們借以判斷是否少數民族文學的元素基本喪失。作者的民族身份大都隱匿,主人公的民族身份未加說明,作品失去了明顯的少數民族地域標志,也沒有相應的民族習俗或者民族符號作為提示。然而,如果深入了解作家的生平以及作家的成長經歷,會發現,他們自身的經歷以及他們創造出來的人物和環境,或與民族身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實際上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少數民族的生存生活狀態與過去相比有了巨大的差異。沿用傳統的思維,將少數民族圈定在傳統的聚居地和傳統的文化圈中,無異于畫地為牢或者刻舟求劍。我們必須注意到少數民族文學匿名的存在,注意到少數民族在新時代的新變化,唯其如此,我們才能發現新世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看到新世紀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深刻性和復雜性,看到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在建構中華民族國家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李詠梅黃偉林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